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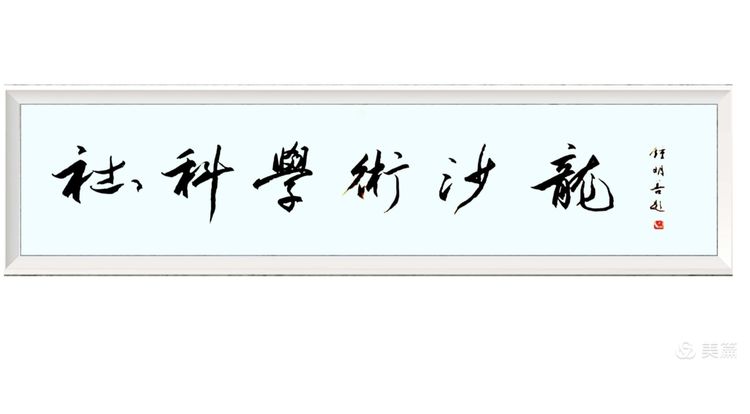
董乡哲老师近照

石鲁画论浅析
文/董乡哲
提 要:石鲁画论之求活求变原则作为长安画派的创作方法论,被应用于笔、墨法中,最终归结为将物化为我,我化为笔墨的物本、意变理念。而其统一观,首先体现为生活与情感的统一,强调用心作画;其次,主张真善统一,强调背画和善于思索。再次,讲究形神统一,强调生活体验的神交和艺术概括上的形简,最终取决于意与理、与法、与笔墨之统一。而且,其新与美的统一绘画理念,不但进一步强化了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理解和捕捉艺术美的重要性,更强调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画论还倡导艺术创作要为生活代言,以情求生活,并将形象分为自然、艺术两种,强调创作要具有可视、可想的功能。既要继承,又要适应形势。从鉴赏的角度看,判定绘画作品是否新颖还有赖于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正确认识。
关键词:求活求变;统一观;生活基础;造型重点;形象神似;情求生活

石鲁先生作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为立意新、表现手法新、技法新、色彩新和画论的创新。其中,对画论的创新则是其作品创新的理论基础。细研石鲁的几次讲话及其《学画论》便可从中看出其中所充盈着的,深刻的哲理蕴涵,且贯穿于绘画创新的整个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总体说来,其画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石鲁画论的灵魂——求活求变
《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处于区域文化中的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画论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其深刻地影响。《易传》认为,易就是变易,正所谓“生生之谓易”、“通变之为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穷则变,变则通。”即运动变化就是事物的普遍规律。石鲁先生首先将《周易》变通理念成功地运用到对人的思想方法的诠释。他说:“人为灵也,才辩阴阳黑白分数定位为之,原太极主而动,思,始以真善而变化为美也,”接着又具体运用到绘画创作理论上面。他认为:“八卦者,画之代数也,……合于太玄,画之哲理也。”
继而,从《周易》中生发出来的求活求变的原则首先表现在石鲁先生对长安画派作品的定性上面。他在6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说:“我们的作品称之为习作,确实因为我们的画都还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对绘画作品定义为“习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使长安画派的画家们产生满足、知足感。因为艺术以“古为流”,“顺流而探源”,则会“长流不息矣。”正所谓艺无止境矣。所以,对传统的继承是不能轻易一竿到底的持续发展过程。同时,对生活的体验也是一个“时刻不容偷懒、僵化、保守”的过程。从创作态势上看,要始终保持艺术创造的后劲,即有了经验还要求经验。即便是在临终前也要求长安画派的画家们保持“探索,不断探索!”的动态创造姿态。
其次,将求活求变原则成功运用到绘画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认为绘画创作过程中充满着变数。在将意在笔先传统理念诠释为外功(表现技巧)受内功(艺术思维)支配的新理念的同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还发现,往往在临池动笔的时候“有时反倒变了”,“每次都得把经验重验一下”。这个发现不但弥补了传统画论的不足,而且体现了极强的可操作性。是对理论与实践临界点状态的科学描述,也是求活求变原则在绘画创作实践过程中的首次闪现。就具体的艺术创造方法而言,要“与古为徒,画观其变,以变寻迹心。”处处充满变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又推衍形成绘画运动观。他说:“中国画讲真,……就是从运动里面来看人,从运动里面来掌握事物,从发展过程来掌握事物。”所以“物与画互为依存转化,谓之运动观。”最终要达到“以真善变化为美也”的结果。
再次,从笔墨方面看,石鲁先生认为:“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因为“依活意而为之则一个万样,死法则为之则万个一样。”对于观物来讲,只有“当面观,变动观……无微不至,必熟才能活。”而观察生活“既要冷观静观,……凡物之形质动静神情姿态,若石能活显于心中”反之则不足言画。因此,虽客观物质有相同与不同之处,但在画法上则是“变化多端。”反之,若以某一方法为万能,则“无异于死教条”。具体到中国画,要讲究气,要以对象为源,以我之神为宿,互为寄托,而我之所托又在于笔墨之气。于是“笔无气不活,墨无气则死”,所以,国画之言气在于求笔墨之活。然气之属性亦在于动。即从其创作主体来讲,出于精神者,为力、势、神;出于物质者,则为水、纸性。于是,气因其本质的不同而分为精神与自然之气两种。精神之气(当以韵律求之)生于其韵律之节奏;自然之气(当以笔墨之浓淡、干湿、黑白求之,色之含气、含光,在于水也:色之包神含情在于变也)则生于其笔墨之色变也。总之,造型之法概括其要义,最终“当物化为我、我化为笔墨,然后则活矣。”而就具体的笔意来讲,“笔率形颠,最忌平匀”,且“若无法而有法”,“于僻僻涩涩中,藏活活泼泼地。”其可贵者在于“笔、墨、色”的相生相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所以笔墨之“物为本,意为变”。即主观与客观相互反映之意理相合,且“法孕育其中”,故而“师古当观其变”、“笔趣之谓即在于求活”。最终体现为“讲变化、讲夸张”的艺术手法。为了便于理解石鲁画论求活求变原则,故将其艺术创作过程图示于下:

但是,求活求变并不是没有规矩和标准的,他在六十年代文艺工作会议上曾说过:“一幅画,无论如何变化,其变化根据,是如何能使思想境界加深。”从而为绘画创作与创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之“艺求法则,虽以统一为定法,然矛盾变化则为活法。笔趣之谓即在于求活矣。”因此,其所谓“活者求其深”是为使笔力如抛砖落地;“活者求其生”是为了下笔如有神;“活者求其精”是力求画不惊人死不休;“活者求其脱”所谓意在笔先。反过来讲,“笔活”的最终目的则在于“意全则神而明之”。

(二)石鲁画论的基础—科学生活观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美术界同样也面临着抉择。特别是在当时“中国画不科学”的民族虚无、保守主义错误观点影响下,出现了一些“风景画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即兴创作与速写“总是缺乏思想,不能谈风格”的论调。那么,中国画到底向何处去?1955年至1956年,石鲁先生与赵望云先生在访问了印度和埃及后,指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绘画艺术传统,才能使中国画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因为“社会主义内容还必须是民族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遂将长安画派创作活动的行动纲领和创新原则概括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传统即石鲁先生所说的是对中国画根本规律的研究。而生活则是长安画派创新的时代精神要求。他将艺术创作过程形象地喻为“若牛吃草而产乳也”;将艺术作品比喻为“母”(生活)与“父”(传统)所生之子,将创作主体与生活的关系描述为“出新意”与“传精神”;将生活喻为创作之源泉,并将生活定位于创作之首,反之则“死”。1961年10月的“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座谈会给予该年的“习作展”很高的评价,李琦说:“石鲁……真是‘画外求画’,……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叶浅予:“对于生活感受,我觉得石鲁较敏锐,感受深,发现了许多新的表现角度。”华君武:“生活里的美……不仅对画家,同时对看画的人说,都是一种享受。”王朝闻:“画家的创造既是基于生活,却又不停止在生活现象的记录,因而取得了高于生活的成就,”等等,可以说是对习作展作品的创作始于生活的首肯。
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方面来讲,石鲁先生认为搞艺术创作必须“取之于自己直接见到的生活”,因为“不到生活中去就找不到艺术”。同时,要求创作“生活化”,使“生活、创作、研究”三者紧密结合,生活须“广泛接触各行各业,丰富自己的思想感情”对于作品也须“多样、生动地反映生活”。而在创作之初,画家的立意就是要为生活代言,而艺术作品本身又会反过来加深艺术家们对待生活的感情。
但生活不是冷冰冰的描写和观察。要真正了解生活,就要在创作中保持“对待生活的感情”。只要画家“有感情,热爱生活”“熟悉生活”就能够抓取生活中偶然的一闪而过的片断印象。尽管有时是“匆匆擦眼而过,”但却“印象非常鲜明”,其原因是被“打动了感情”的缘故。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画家们虽是为创作而生活,但是,如果纯粹为创作而创作,却反而难以创作出好的作品,而是要真正的深入生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群众充满真心实意的爱,才能在生活中发现好的题材和创作出好的作品来。拿石鲁的话来说,就是要解决好主、客观关系的问题。因为生活作为艺术的源泉,只要持有真心、爱心就能得到生活对你的真正回报。因此,他说生活是画的“源泉”、“营养”、“创作之泉源”、“思想之燃料”、“陶冶我之熔炉”。
但是,生活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能完全如实描写”,故真实的生活只能说是解决了作品的题材问题,怎样表现,还要寻找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对于传统的形式和技法,不能局限于对“某家某派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以传统形成一般规律”。即继承整个中国绘画传统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形式和新的表现方法。又根据特定的内容及形式的不同,要求表现方法也因之有所不同。故“我要有我法”,然而此法“又要与古法的一般规律特点相通”。可是,艺术创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将生活中的艺术原形“借喻于其他形象”。石鲁先生将这种思维的酝酿过程称作“艺术内功”。同时,在创作的时候是要“始终贯注着感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感情不是激情。要在运用所掌握的笔墨技法规律和经验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既要“始终贯注着感情”,又要时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胆大而心细,情激而气顺”才可能“笔成于意外”。才能够长久地在创作中保持这种感情和情绪的状态,这种内在的气质就叫作涵养。综观上述,遂将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动态过程图示如下:

既然生活如此重要,那么,究竟怎样生活呢?石鲁先生为我们指出生活的方向“当随主流”。就是说生活目的要明确,要“为生活而画”。但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是其“为生活而画”并不是指的养家糊口,而是“随主流”,强调“生活”的意义在于艺术为政治服务,并指出以艺术为政治服务为目标,其道路必然十分广阔。认为在生活方式上,要忘我,要真心实意地参于生活,不要当第三者,即是“以情求生活,生活即活”。反之,“置身于生活斗争之外者,艺术之智慧与灵感不会降临在冰冷之头上。”只有将“生活移入内心”,进而经主观概括后才能升华为题材。但不能够走马观花,贪而无厌,而要仔细体味“细而不烦”,要淘金,要“观察体会,以类万物之情。”掌据生活之精华。在这里,主要是解决作者的世界观的问题,是解决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和艺术发展方向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使作者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更理想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具体来说,观察生活要如赏画,要当留心,要所受求全。在方法上要全面,如冷观、静观,热观、动观、直观和默观;对所观察对象要有“变动观、上下观、远近观、四时观、表里观”的全方位的观察法。要掌握“以小观大,以深量宽,以细衡整,”并要对观察对象的“形、质、动、静、神情、姿态”等因素烂熟于心才行。否则“不足以言画”。

(三)石鲁画论的核心——辩证统一
细研石鲁的几次讲话及《学画论》等文,便可从中看出其中所充盈着深刻的哲学思辨。可以说这些哲学思想对他的画论与绘画实践的创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其画论诸多理念中,石鲁先生更多强调的是统一的观点。如生活与感情的统一。因为“刻意求生活,生活则不活,以情求生活,生活即活”,故只有感情与生活较好地相互统一,才能“抓取生活中偶然的片断印象”,只有吃进生活,然后才能吐出艺术。而外功作为艺术表现的方法要受内功即艺术思维的支配才能“笔成于意外”。于是,对于画者与物来讲,石鲁认为,“凡物皆有心,画者亦有心,只有心心相印,才能心照而宣。”因而用心去画是很有道理的。再如,他对真和善的理解,所谓真就是要“练成照相机的本事”,“灵活得像是立体的现代电子式的”,“一看就记住了,就能背着画出来。”这便是对客观对象的无限度接近。中国画如果达到了这一步,就到了“自由王国”。而“善”则是主观上的善于思索、分析和提炼,而石鲁先生讲真善(客观和主观)统一的真正意义就是要求达到艺术上的美,即其所说的一加一等于三,也就是由客观与主观结合所创造的一个艺术载体。石鲁先生讲形与神的统一,就是讲的主观对艺术作品的再创造,即从“形—神—形”的个别到一般过程,到“神—形—神”,的艺术提升过程,进一步强调了形的主、客观性和神的主、客观性的统一。可以看出,此处的形、神关系在经历了艺术提升后,变的亲密无间。为了说的明白,在这里不妨将之图示如下:

那么如何做到形神统一呢?石鲁先生主张以神造形。因为,“以神造形,则可变形,”反之“以形求神,则神微。”而形“得神气者为上”。形是神的载体,神藉形以显于外。如若神附于岩石,岩石亦“若虎视而坐威”。而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神贵于全。若使全神贯穿于创作的整个过程,观物时就首先要做到物我感应之神交,次之“沿神而穷形”,后临纸则“入生出神”,如此形神“出乎一意,统乎一笔”。进一步讲,神性属动,“瞬间即变”,在具体观察过程中欲摄其神,则需“察颜观色”,故谓“神当动观”。虽神有“以动制静”的功能,但神是否得以凸显,仍需形的相助,正所谓“形简而神赅”。但“形之简非少”,即“当成型”、“当得宜”、“当愈精”。另外“求形之真,乃以全神贯之,……是谓多样得于统一也。”也就是说,要做到形神统一,首先就要做到生活体验的神交,其次就要在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做到形简。而对形的求简“乃由万眼而来”,“当穷而后工”,后“以神导之”,如此“当删减拨要,概括其质,归为一体,塑为仪式,神则明矣,形则精矣。”
形神一体,神之所以有如此的功能和作用,则缘自于“意为之”,而意作为万物之同一性,若被自由掌握,就能“缘此知彼,有斗量之能”,继而“可谓通灵乎。”故谓神全于“得意”、“情显”、“味长”、“不了了之”、“通情”。从理、意关系上看,“理为客体,亦可谓母体;意为主体,亦可谓父体;法为变体,亦可谓子体。夫理虽为本,画岂能尽各物之理,徒制标本耶?故理必归于意”所以,要真正做到形神统一,须先意理达到统一。
从其方法论上看,石涛《画语录》云:“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石鲁先生发展了其“一画”之理,认为“一画”乃为艺术之哲理,是自然社会之间,事物多样矛盾的绝对之理,要“于矛盾中求统一,统一下展开矛盾”,故“求法乃期于意理、通于众美,而先无法求有法,再化为无法,”而法必以当代形象为本。又谓“若帛之有经纬然,神意为经以立骨,理质为纬以生肌。……故交织之术,乃求不同之同以为和,即以矛盾破统一,以统一驾矛盾之搏斗中也。”故“吾人观乎自然之纹理线条,千差万别,繁杂无章。善于从繁系中理其脉络而成章,……毓一于一画”。上述正所谓意法之统一矣。
具体到笔法来讲,石鲁先生认为“余则谓取诸一般而定体,……则以一治万,以万治一矣。”而“体者,乃一画之谓,骨法之本义所在也。若以一画为连绵不断之意,骨法为抑扬顿挫之法,则笔墨何以能总其艺耶?”,“所言体乃骨者,盖得其体则全其神,得其神骨则显矣。”故谓其功为“一体之谓也”。然而,“体有强健、孱弱、高低、邪正、美丑等之别”,又取决于受、识、意、理,主、客结合的程度。故笔墨之法全在于“当以主客统一、神形兼备为准则”;在于“运笔成风,自成格韵,乃为笔墨风格之集中体现,情态物理溶为一体,统一变化之高度和谐”。同时,“笔墨有无风格乃有无生命呼吸之验,一呼一吸,乃成感化之力,情意之交。故云笔墨为艺之总归,乃在于斯也。故求笔墨当归于性情,归于意志。”即意与笔墨之统一。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形神之统一又取决于意与理、与法、与笔墨之统一。
又如新与美的统一。石鲁先生认为在艺术创作上不断追求新与美,是“艺术反映生活的根本任务”。新与美在哪儿呢?它植根于理想与现实中。关键是我们的艺术家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去汲取。其新的意义在于作者“是否能够抓住现实发展过程中最富有本质意义的环节。”继而进一步用特殊的形象塑造体现出来。而用以检验艺术作品是否新的标准就是看她能否“真正的能给人以精神的的满足与激奋”。那么如何抓住生活中的新呢?其一,只有对人民生活的“爱愈深、愈热情、愈富有理想”其思想“愈新、艺术也愈美”。其二,能否出新还在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是否透辟”。但是只是新还不够,内容新而“形式不美,常使作品平庸无力,不能打动人心”。因为,新主要是指题材、内容方面的状态,是对生活的提炼取舍,还没有上升到美的阶段,只有寻找到与新内容相适应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体现出美的效果。然真正的美,不纯粹是为了满足于欣赏的快感,而是具有陶冶和教育人的作用,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高昂。判断一个艺术作品美不美,是“根椐艺术形象的效果来判断的”,所以新与美的统一实际上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画作欲达到的预期效果,一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结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强烈地吸引着观众”。二是要求“形式也属于内容,常常在追求内容的同时,形式也在构成中”。三是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谐,才能收到政治教育的效果。综上,衡量一个艺术作品新的程度,不光取决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谐的程度,还取决于形式上的标新立异,因为“崭新的形式的出现,又取决于崭新的内容。”是要根据内容的需要,大胆地在形式上创新。这就是艺术发展的法则。同时,认为“探求表现新内容的同时,形式必然起着相应的变化。”因此说,探索内容的新是根本,没有内容的新就不可能出现形式的美。反过来说,形式的美产生于内容的新,反过来又服务于内容的新。于是新、美的和谐统一与否,是作品能否创新的关键。

(四)石鲁画论重点——造型论
绘画艺术作品最终要以一种具体可视的造型形式所体现,那什么是造型呢?石鲁先生将其定义为“创造形象之形式也,”而从型与形的关系上来讲,“形为型之具体化,型为形之程式化,”若有型无形则类似于公式化。故对于形来讲:“当细微”。所以,在其画论中对于形象之论着墨甚多。而形象分为自然与艺术两种,在性质上前者为本,后者为变;在表现形式的属性上,一为真,一为美;在理论上,一为具体,一为典型。而后者却是经主观理想与抽象认识之化合形成的变体,即“为主、客之统一”。从性质上说“抽象为隐,形象为显”。创作主体要对两种形象先后进行主动整合,先是动态的摄取,而后在前者基础上进行美的塑造。故而,作为个别包含一般的艺术形象又可称之为“灵魂与血肉之统一体”。长安画派在其《习作展计划》中对其展品专门提出对艺术形象的创作要求,即作品须“具有自己真切的感受、诗化的意境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可见形式对于艺术作品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艺术作品所要反映的内容、题材等都要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体现出作品的教化作用。对于此,石鲁先生认为“有了生活内容之后,形式便成了决定的关键,”并“具有相当决定性的意义。”所以,画之形象在其功能上因其具有可视、可想之功能,故视之可以通真、通情。并且,为了保证形象的艺术生命长久不衰,就要坚持“贵在典型而生动”“当宁新勿旧”的创作理念。
但形式创新的依据并不是凭空而来,是要有所继承的。是要在“继承美术的传统上,重点还在于形式,特别是技法规律”。但继承不是模仿,而是要掌握“传统形成的一般规律”以及古人“根据彼时彼地的感觉、材料而创造出的表现方法”。因此,“探索新形式首先要从表现方法开始。”但此时的形式并不万能的,它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另一方面又要适应于当前内容的需要。因此,表现方法的多样性要求通过艺术思维使理想与现实、情与理达到基于真实的、美的艺术统一。因此说“造型是思维之活动过程”。
在艺术思维中“现实是基础,但理想起主导作用”,而理想要以生活为基础,理想与想象(想象力伴随理想出现)常通过联想来体现。故“诱人想象者是诗的因素”,因此,画家就像一个诗人,不过是用“直观形象来写而已”。形象作为对生活的概括,对它的创造,还必须靠形容。具体地来讲有比拟、借喻、联想和侧写等方法。但对形象的比拟与借喻要恰如其分,要与真实感连在一起。于是,联想就是深化思想的方法,侧写却要揭示意义最宽最广的那一点。其表现方法的多样性就在于“由生活的复杂性、画家的个性和生活经验的不同所决定。”因为“只要作者对现实生活具有正确的认识,选择富有诗意的景物构思,构思愈独特,形象也就愈新颖”。故此,石鲁先生将整个艺术思维过程称之为“当以意、理、法趣思之”,是谓“物熟而生意、意熟而生艺,艺熟则生术,术熟而生美”。所以熟则是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的核心理念。置此,将其整个造型过程形容为“若饮食然”。
对于造型,石鲁先生一贯重神、重意。他认为神之所以为神,是因其是“具体形象之精神状态所在。”而神与形的关系是“形者,神之载也,神乘形成游焉。”所以,若神附于岩,则“虎视而坐威”,若神附于人“亦可庄严雄伟”。另外,在对待形神的态度上,若为了造型而造型则不知何为画。故形之简在于减繁括质,然后“以神导之”以至形神兼备方可。同时,其形之变在于“去华存质”,故质为神之内,神为质之表。其质乃为形之尺度。而形质一致则是美学尺度。在对尺度的把握上,不仅在结构上“比例相宜,唯求肖似,”且在内容上要“合乎性格和美感”。要做到这些就要做到“眼准手准”,要求画家的眼睛要具有尺子的功能,观乎其美的尺度是否“形质一致”,及其神在形与型的动态关系中是否合度。尽管如此,对艺术的最终检验标准还是掌握在观赏者手中,要观其是否合度及神质并俱,还要以能令“观者睹之不禁动情为验。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掌神自如?他认为要始于观物时的“物我感应莫先乎神交”,类似于“观察体会以类万物之情”之说,反之若无神则“虽视亦无睹”。若能化物为神,而“我则沿神而穷形,以动而制静。”正所谓潜移默化矣。对于此,石鲁先生动地描述为“如此想象翩翩,凝神聚思,以临纸素则入生出神,形不克神,神不离形,出乎一意,统乎一笔矣。”综上,其造型法可分为两个过程,从主观来讲是思维过程:神(我与物神交)—形(凝神聚思,想象翩翩)—神(临纸素出神而形出乎一意)。正如其所讲:“我之观物,先神而后形,由形而复神。”通俗地说绘画创作是由物(客观事物)到意(物化为我,经过主观加工)再化为物(化为物意统一的艺术作品)的转化过程。然石鲁先生对“神”的定义不仅如此,从观物阶段来讲,要“首摄其神”,正如苏轼所讲:“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敛容自持,”正所谓以静取形,以动观神。其次,缘自板桥诗,推而论之,“凡形繁必没神。”是谓“形简而神赅也。”即“笔愈减神愈全”。因为,神之充盈在于得意、情显、味长以及不了了之。然而,形简也并不是无限度的,而是要有其法度,而其法度乃在于成型,在于得宜,在于“尺度精确”,故而“简不寓繁,静不寓动”。
对于具体造型方法来讲,石鲁先生在论及“由整及细、由一及万、由大至小、由简及繁之发端也。”后,总其由为“亦经历史社会之实践与乎一般共感而成”,总其艺为统一之共鸣,“乃共感之综合也”。并进一步以字型由、甲、申、田、用、国、目、风等人像来类比。而对于形之细,他认为其细者即“求多样之统一也。”对于形之“宜”须处于合理状态,即“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对于形之求简在于“尺度准确”,即使是要夸张也要合理。具体地来讲,只要“尺度相宜,固得和谐”。其一是要很好地掌握错觉。其二是要重线。因为只有线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从而构成各具特色的书法及绘画作品,从而体现出无限的客观形象以及美感。故线不愧“为客观形象与主观情感交织之要术也”,所以说“唯线可兼物象与精神也。”综上所述,造型就是在总体上经过先物我相化,后我化为笔墨的创造过程。并强调具体操作时要在“意、理、法、趣俱具”的艺术思维指导下经过“取神、造型、变色、和韵”的创作过程方可成功。

参考书目:
石鲁《学画录》,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
石鲁《“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座谈会》,1961年10月1日。
石鲁《怎样学习传统》,1979年1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的讲演。
石鲁《谈生活与创作》,在《文艺工作坐谈会上的发言》,1960年。
石鲁《新与美—石鲁再谈美术创作问题》,《思想战线》1959年第42期。
梁鑫哲《长安画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247页。
石鲁《西安美协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创作计划》,1961年4月7日。
石鲁《“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座谈会》,1961年10月1日。
石鲁《新与美》,《思想战线》,1959年第42期。

作者简介:
董乡哲一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
董乡哲,男,1954年2月岀生,陕西西安人。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聘为研究员。研究方向:唐诗与传统文化等。
自《试论薛涛之姻缘》一文后,相继发表了《元薛关系新探》《薛涛其名.薛涛心理模式初探》、《薛涛心理模式再探》、《突破惯性的多维考察》、《浅谈古秦王的东方情结》、《回归自然.谈中小企业制度改革》、《不仅仅是要进一步税改》等论文。其中《突破惯性的多维考察》一文,首次将物理学中惯性概念纳入哲学范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还有《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述略》、《论长安画派的创新精神》、《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述略》、《阿赖耶识探源》、《茶文化与佛教漫谈》、《石鲁画论浅析》、《 大兴善寺前身——陟岵寺探源》等论文发表。
曾主持国家课题《黄天厚土.诗经与楚辞的民族文化背景研究》,西安市课题《西安科学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获二等奖。
曾参与梁鑫哲《长安画派研究》、王友怀《昭明文选注析》的编纂。专著《薛涛诗歌意释》、《温庭筠诗集译意》、《鱼玄机传》、《张枯诗集译意》、《孟浩然诗集译释》、《皮日休诗集译意》等书所阐述的观点,更是站到了该学科研究的最前沿。
董乡哲作品欣赏:










(责任编辑 姜丹)